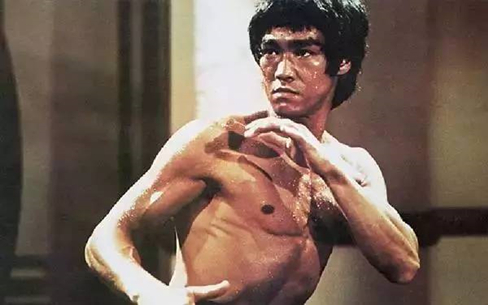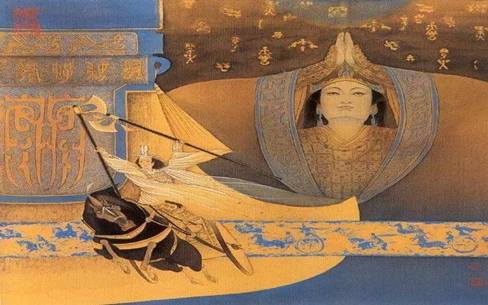我的武术师父是农民

一
难忘少年学艺时
师父姓孙,名润年,我们都叫他润年爷爷。他的院子和我家的挨着,但中间的一堵墙不知什么时候就倒掉了。所以,从我家出来,走几步,跨过那段墙基便到了他的院子。师父的院是长方形的,正房三间,住的是他远房侄子,师父住两间东房,无西房,也无南房。南面是块空地,种着瓜果蔬菜,院中则是、我们练拳的场所,每当清晨、傍晚,总有七八个小孩在那里挥拳弄棒。场地不大,但打弹腿,练绵掌,排成三行,八九个人能同时打。舞大刀,扎花枪则排不开,只能一个一个地来。
那时我十一二岁,社会上正在“闹革命”,学校里几乎不上课,我们一群小孩对练拳倒很感兴趣。我在这里学会弹腿、绵掌、扑虎、八势、缠丝刀、琵琶棍、疯魔枪等多种套路。师父教拳总是先让我们柔腿、压腿、踢腿、冲拳、推掌、扎马步,身上发热之后,才练弹腿、绵掌以及器械等。
弹腿是入门拳,基础拳,练好了才可练其他拳,一般的小孩总要练一二年。那时练拳不像现在放什么音乐,喊什么口令,多是大的在前面练,小的跟在后面伸胳膊弄腿,跟着跟着就会了。师父教拳既严格又和善,看到谁的姿势不正确过去扶一扶,拨一拨,或做做示范,讲讲用法。现在想起来,师父虽是个识字不多的农民,但他教拳的方式还是很科学的。
二
绕师膝下叙传承
从我记事起,师父就是一个人。他有个女儿,我们称金芳姑儿,嫁给师父的徒弟周完喜,但他们比我们大,事情多,有时会过来看一下,也会指导我们练会儿拳,但多数时间是我们和师父在一起。遇上阴天下雨,师父不到地里劳动,我们也不能练拳,便会凑到师父屋里听师父讲一些本门传承、武坛轶事。
听师父讲,我们这门武术是武承州师祖所传。武师祖,文水武家寨人,少时在京学商,得一山东拳师传艺。他有几位出名的徒弟,一为大城南康有金,一身硬功,刃不可侵,曾为太谷曹家、祁县乔家保镖多年,还和武承州师祖进京面见过山东师父;一为我师父的父亲,觉尘师,聪慧过人,尽得祖师真传,但因早年患眼疾,双目失明,几乎过着隐居生活;一为武午村广师,一身轻功,眨眼之间能攀壁上树。据传,武午村有一户在祁县一带经商,受当地几十个村民围攻。广师出面调停,拿根旱烟杆一拨拉,好几个领头手中的铁锨、钉爬都掉到地下,平息了一场武力械斗。还听说左二把的孙子左秉信(人称印师)也向武承州师祖讨教过武功。
多年来,我所疑惑的是,左家印师怎会拜武承州师祖为师呢?近年收集一些武术资料得知,武承州与左昌德是同一时代人,并都在京城学艺,交情一定不薄,让孙子向武学艺是近乎情理的。并且许多资料显示,清末民初,文水武术界已摆脱门户之见,互相学习交流的气氛很浓。不少拳师在乡下设场授徒,好些学校也开设武术课,弹腿、绵掌这些拳应该就是那时的普及套路。上世纪90年代初编撰的《文水县志》中也说:“本县练长拳的都练弹腿和绵掌,人们称这两套拳为文水的看家拳。”
三
睹物思人,师父赠我的刀和剑
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师父的武术器械。花枪、春秋刀和白腊杆别在屋中的一根方形顶柱上。花枪的红樱已有些脱落褪色,但枪尖很锋利,枪杆被手汗浸淫得泛红发亮;春秋刀木柄为红色,刀面黑里透着寒光,据说此刀在闹义和团时饮过人血,所以我们摸一摸都觉有一股寒气。其他的短器械,刀、剑、钩、拐都放在供桌底下,供桌前面有一桌布,一般是看不到的。每到腊月二十几扫舍,师父就会把这些器械一一摆到院里,打扫、擦摸,再把刀鞘、枪杆上贴上一两幅对联,既显得庄重肃穆,又有些新春气息。那时,我觉得师父是最富有、最崇高的。
在这些长短不一,形状各异的武术器械中,有一种叫双拐的器械较特殊——长约80厘米,一头有个横着的把手,掂一掂沉甸甸的。我见过师父练这双拐,扫拨、搂、盖、转、磕、架、拦,虎虎生风。可惜师父没传给我们,这也许是人们所说的留一手,但我不这么认为,师父传授武功是根据弟子的资质、特长而定的,有些武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是不会轻意传授的,更何况我们不少学武人迫于生计,自生慵懒,随着时日的流失连师父已授于的东西也会遗忘许多呢!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学校武术兴起。我在交城城内学校组建起一个武术队,并先后两次到文水、离石培训,学习国家规定套路初级、甲组拳、刀、枪、剑、棍等。师父非但没有门户之见,斥责我未对本门武术的进一步钻研,反而先后送给了我一把剑和一把刀。剑是七星剑,略有锈斑,让一位在交城五金厂的家长电镀了一下,看起来明晃晃的,但失去了原有的特色,很是遗憾。
刀是柳叶刀,人们也称顺刀,是我和小伙伴们学拳时常用的那把刀,也是师傅家里唯一的一把刀,我们常把它擦得油光发亮。那时,我觉得这把刀很沉很长,但和我们现在所练的刀比起来却有点短,有点笨了。不过,这把剑和这把刀我至今珍藏着,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擦摸一下,舞动几招,也总会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师父的思念。
四
未尽弟子本分,惭愧至今
前些日子,在微信中看到一篇有关尊师的文章,题目叫《事师威仪》,摘了几句:“弟子事师,师同于父。”“弟子以时赏师,衣物药物,几杖巾拂,覆覆瓶器,米麦果蔬,供其所需,勿使乏少。”“远师百里,一月一省,若师有疾病、老劣、他故,书疏无限。”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;师父的用的、吃的不能让其缺乏;不管多远,要常看望师傅。联系到现在,不少武林门派举行收徒、团拜仪式,送礼、送钱才可学艺。然而,我们那时是如何对待师父的呢?说起来让人唏嘘不已!
师父年逾古稀,一人独居。我们一群顽童,与师为邻。对师父的称谓不是叫爷爷,就是叫伯伯、叔叔,师徒概念十分淡薄。又值生活困难,物资匮乏年代,何能谈得上供给师父用的吃的呢?
只记得我们一伙孩童在大些的孩子的带领下,帮师父扫扫院子,担担水。好像有一两次我们曾利用压岁钱买过两瓶酒和两包糕点送给师父,其他的怎也想不起来了。有一件事,我还记得。一年夏天,师父劳动回来,指着脚上常年穿的略有破损的仿制军用鞋说,我们打拳穿这种鞋最好。
我们那时只是想,这是师父向我们推荐练功鞋呢,就没想到给师父也买一双。现在看到我的一双双黑的、白的练功鞋,一身身绸的、绒的太极服,愈加感到对不起师父。
授权转载自《中华武术》杂志